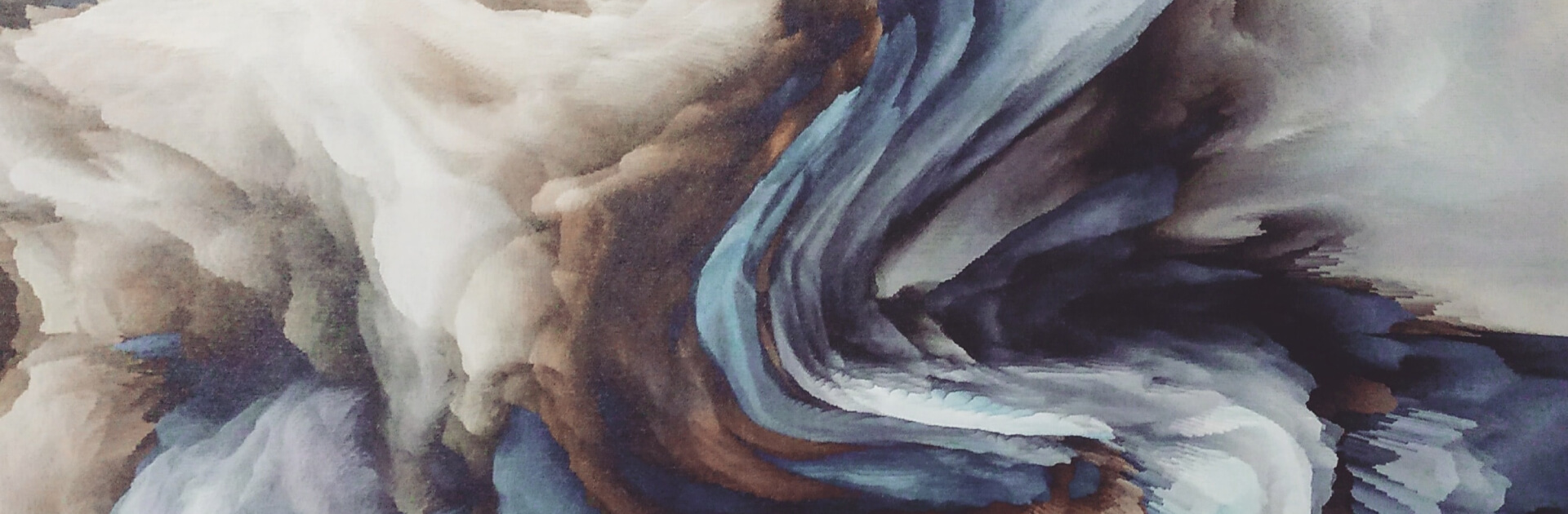

黑白无常,大概为明清时期产生,是阴间的勾魂鬼。关于其来源民间有一些不同的传说。据大谷亨的论文,早期无常可能只表示白无常,后期出现配对黑无常。早期的白无常的搭档不定。鲁迅《无常》中写道白无常伴有一妻子称为无常嫂,儿子称为阿领。(关于黑白无常称为七爷八爷大概是由于维基写的内容为台湾视角、透过网络反传至大陆,将闽南地区的传说覆盖过本土其他地区。)称白无常为谢必安、黑无常为范无救是福建传说,各地有不同的名字不同故事,甚至福建也不止姓范、谢。
通常黑白无常形象带着高帽子,吐出长舌,白无常拿哭丧棒身穿白衣帽子写着“一见生财”“一见大吉”,见到白无常会有发财的可能;黑无常拿勾魂锁身穿黑衣,头上写着“天下太平”,脾气不好,遇到没有好处。
19世纪末《点石斋画报》中白无常戴高帽,手持雨伞、蒲扇,有些挂着元宝,腰间系哭丧棒,白衣披发吐舌,黑无常双手高举如抓人状,黑衣高帽,吐舌披发,有些挂着元宝。由于黑无常特殊的举臂动作,与当时申报中经常与无常一同提及的摸壁,大谷亨认为苏州南部的黑无常由摸壁鬼演变而来。
在丰都天子殿的白无常帽子上为“你可来了”手持蒲扇、雨伞,笑容可掬,与青面鸡脚神放一起,对联写着:“白面无常爷,迎孝接善;青脸鸡脚神,锁恶拿顽。”;黑无常帽子上为“正在捉你”手持锁链,与十大阴帅放一起。在无常殿有无常娘娘。(在清代画像中,四川附近与白面无常褡裆的是鸡脚鬼。)
大公报中《无常》一篇记贵州的吴大爷身高两丈,在城隍庙东,白脸,八字胡,嘴角有一丝微笑,戴一尺高白色长方形高帽,上写“你也来了”或“正要拿你”,白色衣服像如披风,无袖,上下一致,盖住手脚。西面是吴二爷,白衣白冠,黑脸,没有笑容,睁圆双眼。鸡脚神塑像多在吴大爷前面,身材不如平常人高,戴着纸糊的高帽子,项挂纸锭,手执铁链,左腋下夹着一把破纸伞。背微驼,两肩高耸,左脚着地,右脚勾向后方,脚是鸡脚、舌头长长地伸在外面,嘴上、舌头上有黑色鸦片。
《玉历宝钞》的活无常(类似黑无常),死有分(类似白无常),大概为黑白无常的早期形象,活无常头戴乌纱帽,身穿棉袄,拿着纸笔,肩上插着刀,腰上挂着刑具,睁圆眼睛笑。死有分蓬头垢面流着血,身穿白衫,手拿算盘,肩背米袋,胸上悬着纸元宝,紧锁眉头叹息。
在福建台湾的游神中,也被称为七爷八爷、长爷矮爷、大爷二爷、谢范将军,一个身高白脸,一个身短黑脸,高的是七爷,矮的是八爷。是城隍的鬼差,负责接引人死后之鬼魂入于阴曹,又称白无常为谢必安,黑无常为范无救(赦)。手持物与其他黑白无常有所不同。福建地区的来源传说七爷八爷是福州衙门的差役,感情很好,一日,二人约定到南台桥会和,谢必安因大雨未能赶到,范无救在桥下等,因河水涨水不愿离去而淹死(因为溺水面色黑),谢必安因此悲痛上吊而死。(舌头长)
在四川称为吴二爷(无二爷),云南称为二老爹,杭州苏南称黑和尚白和尚,杭州过去也有将无常(指白无常)讹称为扶墙或认为他姓胡,叫做胡干爷,又配了黑脸摸壁鬼、也有将其白衣称为活无常黑衣称为死无常;河南地区称为黑路神、白路神。《越谚》称活和尚、死和尚。
而一進門口所看見的長而白的東西就是他。我雖然也曾瞻仰過一回這“陰司間”,但那時膽子小,沒有看明白。聽說他一手還拿著鐵索,因為他是勾攝生魂的使者。相傳樊江東嶽廟的“陰司間”的構造,本來是極其特別的:門口是一塊活板,人一進門,踏著活板的這一端,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撲過來,鐵索正套在你脖子上。後來嚇死了一個人,釘實了,所以在我幼小的時候,這就已不能動。 倘使要看個分明,那麽,《玉歷鈔傳》上就畫著他的像,不過《玉歷鈔傳》也有繁簡不同的本子的,倘是繁本,就一定有。身上穿的是斬衰兇服,腰間束的是草繩,腳穿草鞋,項掛紙錠;手上是破芭蕉扇、鐵索、算盤;肩膀是聳起的,頭發卻披下來;眉眼的外梢都向下,象一個“八”字。頭上一頂長方帽,下大頂小,按比例一算,該有二尺來高罷;在正面,就是遺老遺少們所戴瓜皮小帽的綴一粒珠子或一塊寶石的地方,直寫著四個字道:“一見有喜”。有一種本子上,卻寫的是“你也來了”。這四個字,是有時也見於包公殿的扁額上的,至於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寫,他自己還是閻羅王,我可沒有研究出。 《玉歷鈔傳》上還有一種和活無常相對的鬼物,裝束也相仿,叫作“死有分”。這在迎神時候也有的,但名稱卻訛作死無常了,黑臉、黑衣,誰也不愛看。在“陰司間”裏也有的,胸口靠著墻壁,陰森森地站著;那才真真是“碰壁”。凡有進去燒香的人們,必須摩一摩他的脊梁,據說可以擺脫了晦氣;我小時也曾摩過這脊梁來,然而晦氣似乎終於沒有脫,——也許那時不摩,現在的晦氣還要重罷,這一節也還是沒有研究出。
鬼魂看读之时,对岸跳出长大二鬼分开扑至水面,两彷站立不稳。一个是头盖乌纱,体服锦袄,手执纸笔,肩插利刀,腰褂刑具,撑圆二目,哈哈大笑,其名‘活无常’。一个是垢面流血,身穿白衫,手捧算盘,肩背米袋,胸悬纸锭,愁紧双眉,声声长叹,其名‘死有分’。催促推魂,落于红水横流之内。
邑某医,夜乘肩舆,路过城隍庙,轿夫忽停步不前。怪而隔帘视之,见二大鬼高俱盈丈,一衣白,一衣青,昂然阔步至寺前。门忽豁然自辟,揖让而入,门复自合。时月色光明,纤毫毕见。归后不数日,医与轿夫四人亡其三焉,独在轿后未见鬼者幸免。 予伯祖母朱氏幼时,其姊患痘,将危。朱入室,见堂中立一大鬼,高及屋梁,白衣高冠。朱惊仆,救起。病月余。其姊于是夕遂亡。
滇人多佞佛,尚鬼神,病者每使巫治之。巫日端公,执旗跳跃,亦有灵时。地多邪神,如小神子、二老爹、鸡脚鬼之类
尝与内子琬君谈鬼,内子云:“其状曩已经之。”因言在室时患喉症,误于医,致成颈创,割治积伤,寝至绵慑。倏忽间魂自棂出,但见天地晦冥,信意所之,不知道里。遇一人,询以何地,曰中州。因具告吴中居址,乞送归,当厚谢。其人许之,遂从之行,徐至家门,人经廊庑,闻家人哭声,不觉复苏,盖气绝已一时许。亟日:“顷有人送归,速谢之。”如言焚镪,自是渐愈。又外
姑彭夫人殁时,外舅梦见,知其已死,因询死状。外姑曰:“ 是夕君等皆出,吾亦卧休。倏见一黑鬼, 盖逮有罪者,拒之。又一白鬼至,则接引无罪者。念数尽不可强留,遂从之。家人聚哭,某为我拭体,某为更袖衣,某为梳发,皆见之,亦颇得自如。”问尚有未了事否,日:“生浮死休,亦复何恋。但二女尚幼,失母可怜。”临去,以花三枝留赠,日:“ 为君预贺。” 盖探花之兆。时内子甫
十一龄,从于孺人宿。孺人廉石先生妾也。一夕微寒,闻彭夫人语云:“风起.矣,胡不为儿辈加衾?”孺人惊觉,声犹在耳,以是调护益谨。后数年,外舅侧生子殇,梦彭夫人抱殇子坐舆中,日:“此非君子,更二年当为君贺。”后平伯内弟生,果如其言。
吾邑有朱桥镇,布市也。贸布者五鼓毕集,黎明而散。忽途人相戒云。 「桥左有一大鬼,高丈馀,白衣冠,被发执扇,眉目下垂,口鼻流血,世所谓无常鬼是也。见者咸弃物奔逃,迟则惊毙。」以故市为改。时庄农王二者,家有急需,不得已,于寅刻携灯负布趋市。至桥左,遥见大鬼昂然来,王骇极,灭灯潜入桑林内,猱升树颠,藏丛叶间。时月色朦胧,鬼不及睹,行至桑林外,喟然叹曰:「明明一人来,倏忽不见,妖耶?怪耶?」语未竟,又一大鬼来,服色面目相等,向前拱其手而过。前鬼曰:「噫,是矣。吾等费心计逐客至此,而为彼所得,当抽分其贷。」遂大唤后鬼回索分也。后鬼瞠目直视,忽扬大掌,拦腰一击,前鬼扑地,首与上下身及两臂跌分五截,俯捏之,得青烟二道。解佩囊纳讫,长啸而去。王二犹不敢下树。至旦,见行人结队来,始呼救,众集而后逼视,则鬼之首系纸糊者,两臂与手削木为之,上身一人、下身一人俱死。纸衣亦裂,始悟二贼顶接作长人,假鬼以行劫,而真鬼毙之,报亦巧哉。



